辽麻餐厅:嬗变中成就美食传奇
- 来源:辽阳市文联
- 时间:2023-05-22 09:55:16
李大葆
辽麻餐厅,伴随一座工厂的诞生而出现,又为这个企业的退场而满怀缱绻和留念。如今,在新时代的风气濡染中,这一处依然用锅碗瓢盆、煎炒烹炸点缀岁月的所在,与时俱进,越发卓然而立,一展风华,让人品咂着岁月更为鲜美的滋味……
(一)
今日的辽麻餐厅,知情人叫它老食堂。
老食堂与当年的工厂同步出现。
二十世纪的三十年代,一个叫小泉德一的日本人来到辽阳。于是,奉家烧锅、下洼子一带将近41万平方米的田野,在一年多的时间里,相继被厂房、宿舍、围墙、道路占据。1939年8月28日,称为辽阳纺麻株式会社的工厂宣告建成并投入试生产。从四面八方“招募”而来的1800多人,成了高墙内的劳工。日方严密的管控机构,繁重的生产任务,不停转动的机器,使麻袋垛越来越高、麻线越来越长,成为受奴役者的脂膏和血泪,被源源不断运往日本。
应运而生的一处劳工食堂,也必然是个有故事的地方。下面这些搜集、整理于1983年的文字,虽然出于亲历者的各自回忆,却不约而同地指向了当时的现场,为同一事物的不同侧面作出了详细的认证与辩白。
故事之一
建厂之初,管理食堂的是日本人米光,在战场上丢了一只胳膊,但凶狠却不见减少。除去常挂嘴边的辱骂,他手中的马棒,不知多少次抡在用餐劳工的身上。如果有谁吃饭时不小心掉了一点饭粒,或损坏了一个饭碗,那就很难逃脱他的一顿毒打。亲历者说:“工人们恨死他了。”压迫的极限处,是反抗。1939年3月1日下午5点多,一位女工桌前有几粒饭粒,米光不问青红皂白,举起马棒就向那女工头上打去。工人陈尚和见状,把饭盒大声地往地上一摔,将米光的马棒引向了自己。陈尚和不断躲闪,其他工友也摔碗的摔碗,折筷子的折筷子;不知是谁还乘机把电灯关了,食堂里一片漆黑,工人们一拥而上,把米光痛快地教训了一顿。闻讯赶到的日本人围住了陈尚和,非得追查出更多的打人者不可。陈尚和坚定地回答:“伸手的就我自己。”混乱中,陈尚和逃出了厂门,很长时间没有在辽麻露面。
故事之二
日本人虽然给中国工人建了食堂,但给工人们吃的却是苞米面、椽子面掺和的窝窝头,磨的很粗的高粱米稀粥,大萝卜块白水汤,生了蛆的咸菜疙瘩。如果“改善”伙食,也仅是将一块豆腐切成四份,每人一份,工人管它叫“牛眼珠子”。1939年8月6日,加油工苏仲元因吃不饱,穿不暖,每天干12小时的体力活,只能挣到两角5分钱,就想辞去工作。谁知他找到社长,不但不允许,反而被踹了两脚、骂了一顿。苏仲元十分悲伤,回到宿舍又哭又喊,后来捡起一块木炭,在墙上写道:“满洲国不久长,小鼻子都快亡,走狗把头一扫光。狗翻译跑不了,男儿立志把仇报。”还在下面画了两幅画:两把尖刀分别插在社长小泉和走狗翻译身上。宿舍是大通铺,住了30多个工友。大家怕这些文字和漫画给苏仲元带来祸患,劝他抹去。苏仲元态度坚定,说:“不抹,随他们便吧。”后来,苏仲元跑回了凤凰城县老家。
故事之三
1945年8月15日,电气工刘启元到食堂吃饭时,因多盛了一点饭菜,被校正辅导院巡视的军官用战刀捅伤左臂。工人们看见刘启元鲜血淋漓,都义愤填膺。朱明玉、刘兴武等30余名工友,向辽阳监狱设在辽麻厂的监所冲去,准备以砸狱放走犯人的方式为受伤的刘启元报仇。监所中的人听到消息后,积极配合,趁势跑出去不少。厂里的日本人曾田、太田、米光等向市宪兵求援。十几名宪兵围住厂房,把机枪架在整理过的麻包上。整理车间800多名工人被集中在一起。在这千钧一发之际,工人代表郭尚志据理力争,日本人也接到了无条件投降的命令,宪兵队也就悄然散去了。以王鹏飞等为首的“犯人”于监所逃出后,组建了东北人民自治军,后来被编入八路军冀热辽军区。
两册关于辽麻建厂之初情况的档案,在阅读者手中颤抖着展开。许多历史,桩桩件件,都与老食堂有关。
(二)
随着1948年10月30日辽阳的最终解放,辽麻回到了人民的手中。
新中国,一切都焕然一新。辽麻迅速完成恢复建设工作。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,这个国有企业年平均职工人数为1709人,生产麻纱433吨,麻袋595万条,实现工业总产值1184万元,获利润313万元。
更可点赞的是,工厂食堂发挥了极大的保障作用。五十年代末,在辽麻职工中流传一首诗,云:
食堂搞得欢,主食天天换。
吃起真适口,肚饱又省钱。
走向车间去,炼钢又办电。
感谢党关怀,保证大生产。
这样浅白的顺口溜,人人都会作,但它却发自职工们的心底,而又实事求是,没有虚妄和夸饰。在当时媒体报道这个企业工作经验的文章中,有这样的做法:工厂把“一手抓生产、一个抓生活的方针”作为工作遵循,为了使“以办好食堂为中心”这个承诺不至于成为空泛的口号,除一名副书记和一名副厂长负专责,以及建立干部下伙房制度,让决策者同食堂人员一起研究改进食堂工作外,厂里还要定期检查,并集思广益,拿出让职工吃饱吃好的真办法。
百废待兴的共和国,全国人民的生活不够富裕。当时,在粗粮供应较多、蔬菜供应不足的情况下,炊事员们粗粮细作,素菜荤做,想尽办法让“职工们欢乐地走进食堂,端起碗来越吃越香”。因而,“他们把苞米面重新磨了三遍,然后用苞米面摊出煎饼,软而筋道;用苞米面做的油糕,又甜又香;其他像酸糕、牛舌饼等也都是味美可口。同时,把汤菜也做的很好,只用大萝卜就做出五样菜;其他,酸茶、胡萝卜、豆芽等二十多样菜,也做得很有滋味。”(《麻袋厂食堂有起色》,《辽阳日报》1959年1月22日二版)
岁月连环,尘世纠缠。
煎炒烹炸,在偌大厂区的一角释放着缕缕馨香,又渐渐汇入织机隆隆的车间。
如今,许多老工人对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辽麻老食堂的情景还记忆犹新。那时,炊事班有三四十人,面案上的、菜墩上的、掌勺的、主灶的,都是在全市也拿得出手的师傅。职工三班倒,赶上饭顿的,三餐不空。哪一班都有三四百人就餐,工友们一拨一拨潮水般来去,饭菜的香味久久不散。
到了八十年代,食堂有24张桌子,每张桌子安装8个连体凳子。虽然有人把饭菜端回办公室或车间去吃,但大多数人还是愿意在食堂凑热闹。在食堂就餐的,熟识的往往凑在一起,先把各自的菜盘往中间一推,不分彼此,互通有无;再把连体板凳从桌面下拉出来,稳稳当当坐上去。“这么多嚼骨儿,能啜两口多好!”“得了吧,还干活不?”大伙嘻嘻哈哈地边吃边逗闷子。
就餐的人在窗口往往会犯一阵儿核计,主食有米饭、花卷、馒头、包子,哪种都有食欲;一二十个菜盆,一二十种菜,在台面上展开,挤挤挨挨,晃花了人的眼。
改革开放的大潮,不断把时代的面貌刷新。老食堂位置没变,但它所呈示的景象,却越发不同凡响了。1989年企业推行承包经营制,刘剑受命接过辽麻的老食堂。
那时,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,店铺开张谁都图个红火,取名也时兴大的、洋的,人们劝刘剑给食堂取个打眼儿的名字,便于面向社会经营。而刘剑呢,犟,就看好“辽麻餐厅”这四个字了,顺嘴。有人递来一张纸,密密麻麻写了四五十个名字,刘剑一笑了之,还是叫“辽麻餐厅”,山呼海啸奈若何!
“辽麻餐厅”四个字,是历史用苦辣酸甜积淀的结果,是走了多远、多久也不改身份的坚定告白,也是它的继承者对一枚老字号发自心底的敬畏,以及恭恭敬敬的承接,它让人感知了一就是一、二就是二的纯朴和敦厚。
花里胡哨的名字,能代表什么呢?好味道,才是一家餐馆得以延续的根基……刘剑说。
刘剑敬畏的是“辽麻餐厅”身后的历史支撑!
(三)
有议论者称赞辽麻餐厅是“锁住传统味道的美食集结地”,并不过分。认识一座城市最好的方式就是逛逛它的菜市,知道这座城市的美味,就是到餐馆去,看看大厨们是怎样用地产的食材,感动了你的味蕾。
刘剑换上洁净的白色工作服,开始新一天的工作。
这的确是全新的一天,一个转身,他将掌门人、厨师长、采购员多种身份集于一身。他深深吸了一口气,又缓缓吐出来。他在灶台和案板前走着,与那些个甘、酸、苦、辛、咸,以及肉、蛋、菜、果、菌,一一照面;与煎、炒、烹、炸、炖,烟、火、汽、水、冰,再度相认。
23岁的刘剑,体会到了自己走马上任的别样的仪式感。他端起了自己命运的饭碗,也要在这只大碗里为大众送上一份特殊的菜肴。
此后,一盘菜,在他手里,还是程式化复制出来的产品吗?他突然醒悟:不!它应该是一份倾注了哲学及伦理的作品。
全国名厨刘敬贤大师表扬刘剑是在用良心做菜。良心是可以把一块石头捂化的真挚与痴迷。
经过十几年的发展,辽麻餐厅的营业面积,由原来的800平方米,增加到4000平方米,拥有4个宴会厅、28间包房,可同时容纳1200人就餐。如今,无论春、夏、秋、冬,辽麻餐厅火爆依然。别说平时订餐电话不断,当遇上节假日,即使座位已满,知味者宁愿站大排也要等,劝都劝不回去,有时服务员不得不把办公室临时改作餐厅,夏天还会把桌子支到院子里的葡萄架下。
知味者就是奔着它的“招牌菜”来的!招牌菜就是本地的“情怀”菜。一家成功的饭店,不应该仅是个顾客吃饭的地方,而应该是有烟火气、有人情味儿的场所,特别是社区类的饭店,应该有街坊邻居的悲欢离合,有家长里短须臾不离的阴晴圆缺,即使是一碗平常的米饭,也应该有十足的“本土味”,有父老乡亲值得永远铭记的感觉。
在辽麻餐厅的菜谱上,一道菜,非千淘万滤不可单上有名;一道菜,若是众望所归,即使利润微薄,做工繁琐,也不可脱单。
介绍几例辽麻餐厅的拿手菜。
——哈鱼饼子:舌尖上妈妈菜的味道。
脱胎于咸鱼饼子的哈鱼饼子,在传统食材的选择上有了苛刻的增删。将原来采用的大连地区的鲅鱼,换成黑龙江流域的马哈鱼,而这种马哈鱼须有两年半的生长期,肉质鲜美,营养丰富;饼子由起初单一的玉米面,改成加入一定比例的白面和豆面,白面让饼子的口感更加松软,豆面则增加了饼子香甜的气息。在继承和创新中,哈鱼饼子承载着怀旧的使命,让人们进一步感受了妈妈做菜的味道。
这种升华,追求的是对知味者口感的跟进和体贴,向老母亲关怀家人一样的在意和付出,难怪有人赞曰:“每一口都饱含着真挚的母爱。”
任何原料,因为不同的加工方式和做法,都会产生不同的口感。刘剑认准了这个理儿。
但这道菜的推陈出新,竟然转身成为辽麻餐厅的独家品牌!为了与咸鱼饼子区分,刘剑将菜名改为哈鱼饼子,“哈”拜马哈鱼之所赐。
——酸菜排骨:难挡的绝佳美味。
有一个数据:辽麻餐厅用于制作排骨酸菜这道菜,平均每天要消耗酸菜约600斤、排骨300斤。这个数据,显示了食材的种类、数量,更对菜与肉的比例一目了然。数据,还足以说明菜品的火爆程度。“翠花,上酸菜!”客人们大呼小叫,欢喜劲儿十足。除了当地人,每天还有许多外地食客慕名前来,就为尝一口这正宗的酸菜排骨的味道。
然而,这个数据却不能道出的还有选材和烹制时的用心良苦。全部酸菜都是在常温水果库中渍制的,这一点圈外人不知道。每天清早,热乎乎的排骨香味早就在餐厅中弥漫补开来,这一点,圈外人仍然不知道。酸菜排骨是经典的东北菜,但要想吃到正宗的味道,可不是一件易事。
排骨融合了酸菜的酸味,酸菜又解了肉的油腻,而且汤也是鲜咸可口、喷香味浓的。过去,这道菜,慰藉的只是东北人祖祖辈辈漫长的冬天,而在辽麻餐厅,它能不能跨越季节的藩篱,无论春、夏、秋、冬,它都一以贯之地给人以口福?
刘剑说,凡事先不要说“不能”。
知味者不看菜单,刚坐下,又是一嗓子:“翠花,上酸菜!”于是,一姑娘马上回了一声,把“哎”字的尾音拖得长长的,流水一样蜿蜒。
这场面,让人服了:餐饮里面还真有文化!
——竹香羊脖:大自然的神奇馈赠。
都说这道菜是刘剑的杀手锏。
羊脖子是“活”肉。知味者说,会吃的人,在羊身上,就选那地方。
但是,羊脖子的做法可多了去啦,清炖、清蒸、红烧、炙烤,还有没有新招法?老饕们对厨神将了一军。
在老饕们与厨神的对抗赛中,这道菜,在辽麻餐厅已经有20多年的历史。刘剑在羊脖子制作工艺上下足了本钱,将老汤工艺与蒸烤技术相结合,亮出一道新品,名字很直白:竹香羊脖。
在选材上,需要当年生绒山羊的羊脖子,要的就是它肉质的特别鲜嫩。在制作中,用竹帘包扎羊脖,目的一是让竹香经过卤制渗入肉中,二是使羊肉更加紧实,保持羊脖的外形,使菜肴更具观赏性。
刘剑进一步亮出底牌:老汤,是煮过多次的肉汤。老汤保存的时间越长,芳香物质越丰富,香味越浓,鲜味越大,煮制出的肉食风味愈美。任何一锅老汤都是日积月累所得,所以便显出格外的珍贵。为了确保菜品口味始终不变,老汤每天都要在保持静态的情况下加热,以保证不损坏汤质。刘剑在老汤中掺入十八味中草药,这样做除了可以起到去腥、去膻、滋补的作用,还能将更深厚的滋味浸入到羊脖之中。
知味者评价说:竹香羊脖外酥里嫩,香气扑鼻,单独食用口感也甚佳,若再配上薄薄的卷饼和诱人的蘸料,就是神仙尝过的人间美味。
如此论道,当是专业美食家的眼光!
辽麻餐厅用几十年的时间,积攒了自己的家底。这家底,就是一个又一个“招牌菜”。除了上面细说的之外,还有:
——笋干宝塔肉、秘制猪蹄,获得过东北三省金牌菜肴、省知名风味菜肴等殊荣。
——卤制驴肉、蒜香鲈鱼、素三鲜饺子等,被评为东北金牌菜。
——红焖猪肉,是“辽宁知名风味”……
翻开“辽麻餐厅”的菜谱,还可以看到数十道精美菜肴的名字,它们共同支撑了辽麻餐厅的荣誉和名片。
“辽麻餐厅”的菜肴,归类于辽菜,辽菜技艺入录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省相关部门确定“辽麻餐厅”为辽菜的传习店之一,并设有旨在辽菜传承和研发的大师工作室。
近年来,辽麻餐厅荣获了许多牌匾和证书,这是他们把事业做向精致的证明——
全国特色餐饮名店;
东三省餐饮名店;
东北菜名店;
辽宁省餐饮名店;
辽宁老字号企业;
辽宁十佳婚庆名店;
辽阳市餐饮名店;
辽阳市社会信赖名店……
一块块牌匾流金溢彩,一本本证书鲜艳夺目,犹如古驿路旁常开不败的花朵,迎春而开,播香四野,灿烂而持久。

2020年辽麻餐厅夜景一角

辽宁省总工会在辽麻餐厅设立创新工作室

1980年代辽麻纺织厂招待所员工合影

2022年刘剑荣获辽宁省劳动模范称号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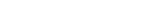 VX:21517825
VX:21517825